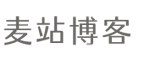象腿女孩
每当想起我人生中不如意的部分,我总是想到那个象腿女孩。
我们相遇在11月夜晚的地下铁车厢。
11月夜晚的地铁简直就像是开在北极的冰面底下一样冰冷,车体冻得咬紧牙关,咯吱咯吱地作响。她站在我的对面,穿着一条绿色的连衣裙,披着一件不搭调的豹纹薄外套,双腿在裙下光溜溜地探出。那是一双矫健的腿,肌肉紧绷着,仿佛随时准备双腿交叉,有力地将某人的脖子绞断一样。
“紧绷的肌肉是生活的象征。”我的脑海中闪出了这句话,好像松弛的肌肉就不应该拥有生活似的。
那天晚上我们上床了,在那之前我们看了一场电影。就像大多数年纪过了25岁的年轻人一样,我们在情感关系愈趋保守的同时,在性关系上表现出反方向的轻率。同样,我这句话好像是说人在25岁后开始堕落,而大多数人能在25岁前保持纯真似的。
老实说(或者显而易见地说),她并非是我喜欢的类型,光是那健壮的双腿就拿到了第一张Pass票。我喜欢的是邻家女孩的那种类型,这大概是从小到大我的邻家都没有女孩的缘故。当然她有可能是别的男孩的邻家女孩,但不是我理想中的、形而上的邻家女孩,在我理想中的邻家女孩总是有着温软的身段,直溜溜的未加烫染的头发,倔强而小巧的鼻尖,配以亲切的微笑,就是那种可以轻盈地将生活中的幸与不幸照单全收的笑容。
那以后我们又看了几次电影,睡过几次觉。我们默默地在黑暗中看电影,默默地在黑暗中做爱,我们都不大愿意说话,她只有在做爱时会毫无顾忌地叫唤,双腿紧紧地夹着我的腰肢,下体温暖而湿润。我们总是在看完电影后去她的家里做爱。她的房间小而简洁,墙体单薄,在冬天的夜晚里就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一样敏感而脆弱。虽然房间里铺着一大块白绒绒的地毯,我还是觉得冷,于是我们总是进门后不久就会一起钻到床上的被子里抱在一起,这时候她身上紧绷的肌肉开始一点点地舒展开来,就像一枚苏醒过来的摇摇欲坠的果实滑入我的手心。
“我叫得是不是太大声了?楼上楼下的人一定听到了。”完事后她总是这样问。窗外飘渺的光朦胧地披在她的身上,依稀映出她涨红了的脸。
“不会的。”我安慰她说。毕竟这不是我的房子、我的邻居,我没必要担心太多。
当然我们之间还是有一些温暖的时刻。比如某个在她的房间里醒来的早晨,看到了阳光洒在窗前,那是那个冬天为数不多的有阳光照耀的日子。我们坐在窗前的一张圆形玻璃桌前,那两张白色藤椅简直就是专门为这个早晨准备似的。
中间她出去了一会,然后提着一袋春卷回来。我不喜欢吃春卷,于是便看着她咔嗞咔嗞地把脆卜卜的春卷一个不剩地吃完。在这过程中,我意识到在这小小的桌子之间横亘着一条看不见的鸿沟,我在这头,她在那头。正如我不会喜欢春卷一样,我永远都不会喜欢上她。而我与她上床恰恰又是因为这一点,我不用担心卷入杂芜的心事和纠缠不清的关系中去。明白了这一点后,一种悲哀的心绪泛上了我的心间,我们人生中太多这样的事了,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,和自己不喜欢的人做朋友,和不喜欢的人结婚、生子。而这样的结果,大多数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。
那个早晨我们谈了很多,也许是我们都意识到我们的关系就要终结了,那种征兆正在某处敲着某个门,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转动门把手走出去而已,问题在于我们要以何种姿态走出哪一扇门。
“嗳,在你的心里,你是怎么叫我的呢?”女孩问我。标准式的结尾提问。
“这个啊……”我的脑袋思索了起来,就像笨手笨脚的熊一样。
“‘象腿女孩’,是这样叫的吧?”
“什么?”我吃了一惊。
“一次都没有这样叫过?‘今天晚上要跟象腿女孩去约会了’,这样的叫法难道没有过?”
“干嘛要这样想?”
“以前的那些男孩都这样叫我。”她摆弄着自己放在桌面上的手,她的指甲圆润而丰满,“没有一个例外。”
“噢!”
“真的一次都没有?”
“没有。”
于是她吁了一口气。
我也吁了一口气。实际上我说了谎,从我见到她的第一眼起,“象腿女孩”这个印象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我的记忆深处。当我闭上眼睛,如果我不用“象腿女孩”这四个字作为线索,我的脑海就不能准确推出关于她的形象、她的容貌、她的姿态以及关于她的一切。
直到现在,我还是觉得我撒这个谎为好。
而究竟我在象腿女孩的心中会是怎样的叫法呢?我之于她是愉快的体会,或是不愉快的体会呢?我没有认真想过这样的问题,毕竟在人生中关于自己的事情,这样的那样的,这些的那些的,要思虑的已经太多了。
我们相遇在11月夜晚的地下铁车厢。
11月夜晚的地铁简直就像是开在北极的冰面底下一样冰冷,车体冻得咬紧牙关,咯吱咯吱地作响。她站在我的对面,穿着一条绿色的连衣裙,披着一件不搭调的豹纹薄外套,双腿在裙下光溜溜地探出。那是一双矫健的腿,肌肉紧绷着,仿佛随时准备双腿交叉,有力地将某人的脖子绞断一样。
“紧绷的肌肉是生活的象征。”我的脑海中闪出了这句话,好像松弛的肌肉就不应该拥有生活似的。
那天晚上我们上床了,在那之前我们看了一场电影。就像大多数年纪过了25岁的年轻人一样,我们在情感关系愈趋保守的同时,在性关系上表现出反方向的轻率。同样,我这句话好像是说人在25岁后开始堕落,而大多数人能在25岁前保持纯真似的。
老实说(或者显而易见地说),她并非是我喜欢的类型,光是那健壮的双腿就拿到了第一张Pass票。我喜欢的是邻家女孩的那种类型,这大概是从小到大我的邻家都没有女孩的缘故。当然她有可能是别的男孩的邻家女孩,但不是我理想中的、形而上的邻家女孩,在我理想中的邻家女孩总是有着温软的身段,直溜溜的未加烫染的头发,倔强而小巧的鼻尖,配以亲切的微笑,就是那种可以轻盈地将生活中的幸与不幸照单全收的笑容。
那以后我们又看了几次电影,睡过几次觉。我们默默地在黑暗中看电影,默默地在黑暗中做爱,我们都不大愿意说话,她只有在做爱时会毫无顾忌地叫唤,双腿紧紧地夹着我的腰肢,下体温暖而湿润。我们总是在看完电影后去她的家里做爱。她的房间小而简洁,墙体单薄,在冬天的夜晚里就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一样敏感而脆弱。虽然房间里铺着一大块白绒绒的地毯,我还是觉得冷,于是我们总是进门后不久就会一起钻到床上的被子里抱在一起,这时候她身上紧绷的肌肉开始一点点地舒展开来,就像一枚苏醒过来的摇摇欲坠的果实滑入我的手心。
“我叫得是不是太大声了?楼上楼下的人一定听到了。”完事后她总是这样问。窗外飘渺的光朦胧地披在她的身上,依稀映出她涨红了的脸。
“不会的。”我安慰她说。毕竟这不是我的房子、我的邻居,我没必要担心太多。
当然我们之间还是有一些温暖的时刻。比如某个在她的房间里醒来的早晨,看到了阳光洒在窗前,那是那个冬天为数不多的有阳光照耀的日子。我们坐在窗前的一张圆形玻璃桌前,那两张白色藤椅简直就是专门为这个早晨准备似的。
中间她出去了一会,然后提着一袋春卷回来。我不喜欢吃春卷,于是便看着她咔嗞咔嗞地把脆卜卜的春卷一个不剩地吃完。在这过程中,我意识到在这小小的桌子之间横亘着一条看不见的鸿沟,我在这头,她在那头。正如我不会喜欢春卷一样,我永远都不会喜欢上她。而我与她上床恰恰又是因为这一点,我不用担心卷入杂芜的心事和纠缠不清的关系中去。明白了这一点后,一种悲哀的心绪泛上了我的心间,我们人生中太多这样的事了,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,和自己不喜欢的人做朋友,和不喜欢的人结婚、生子。而这样的结果,大多数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。
那个早晨我们谈了很多,也许是我们都意识到我们的关系就要终结了,那种征兆正在某处敲着某个门,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转动门把手走出去而已,问题在于我们要以何种姿态走出哪一扇门。
“嗳,在你的心里,你是怎么叫我的呢?”女孩问我。标准式的结尾提问。
“这个啊……”我的脑袋思索了起来,就像笨手笨脚的熊一样。
“‘象腿女孩’,是这样叫的吧?”
“什么?”我吃了一惊。
“一次都没有这样叫过?‘今天晚上要跟象腿女孩去约会了’,这样的叫法难道没有过?”
“干嘛要这样想?”
“以前的那些男孩都这样叫我。”她摆弄着自己放在桌面上的手,她的指甲圆润而丰满,“没有一个例外。”
“噢!”
“真的一次都没有?”
“没有。”
于是她吁了一口气。
我也吁了一口气。实际上我说了谎,从我见到她的第一眼起,“象腿女孩”这个印象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我的记忆深处。当我闭上眼睛,如果我不用“象腿女孩”这四个字作为线索,我的脑海就不能准确推出关于她的形象、她的容貌、她的姿态以及关于她的一切。
直到现在,我还是觉得我撒这个谎为好。
而究竟我在象腿女孩的心中会是怎样的叫法呢?我之于她是愉快的体会,或是不愉快的体会呢?我没有认真想过这样的问题,毕竟在人生中关于自己的事情,这样的那样的,这些的那些的,要思虑的已经太多了。
上一篇:末等生 下一篇:没有了
相关文章
- 2018-02-15淡,是一种至美的境界
- 2018-02-15最难的一件事其实叫随遇而安
- 2018-02-15你喜欢的只是那个不喜欢你的她
- 2018-02-15致我们回不去的十七岁
- 2018-02-15如果我欠了你五块钱 请你告诉我